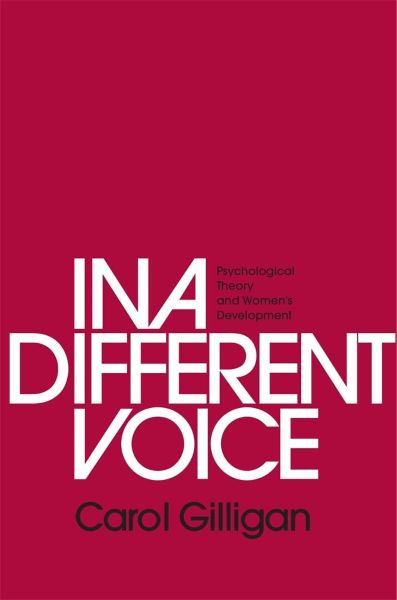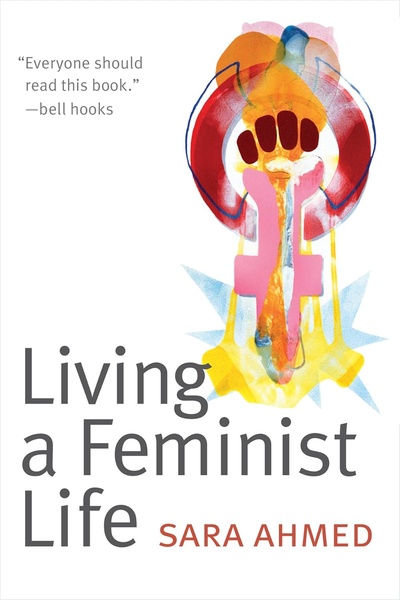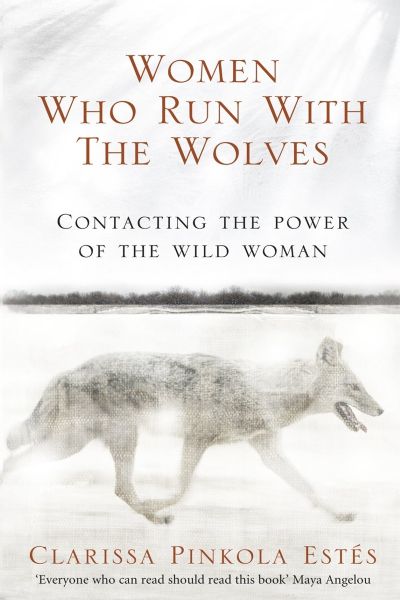好女孩:厌食症的故事与研究
《玻璃之屋》畅销书作者哈德利·弗里曼的回忆录,讲述她14-17岁在精神病院与厌食症抗争的经历,追踪20年后与她一起住院的女性们的康复历程,揭示厌食症与青春期女性成长困境的深层联系。《纽约时报》称其'引人入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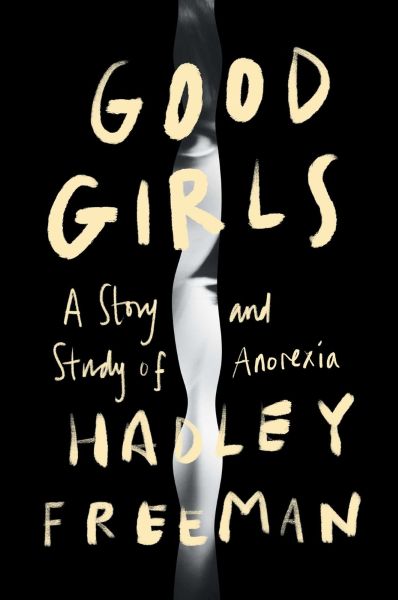
📝 书评导读
1995年,哈德利·弗里曼在日记中写道:“我刚刚在精神病院度过了人生中的三年。那么为什么我现在比以前更疯狂了?”从14岁到17岁,弗里曼在精神病院病房中度过,与厌食症抗争。医生告诉她,她的身体正在分解肌肉和心脏来获取营养,但他们几乎无法告诉她其他任何事情:为什么她会得这种病,这种病感觉如何,康复是什么样子。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弗里曼作为一个”功能性厌食症患者”生活,随着厌食症的变异和持续,她不断与新形式的自我毁灭行为搏斗。《好女孩》不仅是一部关于疾病的回忆录,更是一次深刻的调查研究——弗里曼回到过去,追踪当年与她一起住院的女性们,采访医学专家了解治疗的最新进展,试图理解这种广泛讨论却鲜被理解的精神疾病,以及它揭示的关于女性成长的残酷真相。
哈德利·弗里曼是一位美国裔英国记者和作家,1978年出生于纽约的犹太家庭,11岁时随家人移居伦敦。她在牛津大学圣安妮学院攻读英国文学,担任过学生报纸《Cherwell》的编辑。2000年加入《卫报》,在时尚版工作八年后成为专栏作家,为该报撰稿二十余年。2022年,她转投《星期日泰晤士报》,2024年获得新闻奖”年度专栏作家”殊荣。她的作品还出现在美国和英国《Vogue》、《纽约杂志》、《时尚芭莎》等众多刊物上。她最著名的著作是2020年出版的《玻璃之屋:二十世纪犹太家族的故事与秘密》,这本书追溯了她祖母萨拉和她的三个兄弟在波兰、法国和美国的生活,揭开了家族中长期被掩盖的大屠杀幸存史,成为《星期日泰晤士报》畅销书,在全球出版。《好女孩》是她最私人、最脆弱也最勇敢的作品,将她作为记者的调查技能与作为幸存者的亲身经验结合,创造出一部既深刻又可读的作品。
厌食症是最致命的精神疾病之一,死亡率在所有精神障碍中最高,但它同时也是最被误解的疾病之一。在大众想象中,厌食症往往被简化为”爱美的女孩不吃饭”,被归咎于时尚杂志、社交媒体和”虚荣心”。受害者被认为是肤浅的、自恋的、寻求关注的。这种污名化的理解不仅无助于治疗,反而给患者增加了额外的羞耻感,使她们更难寻求帮助。弗里曼写这本书的首要目的,就是要打破这些刻板印象,揭示厌食症的真实面貌:它不是关于虚荣,而是关于控制;不是关于外表,而是关于内心深处的恐惧和痛苦;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疾病。
弗里曼以极其诚实和细腻的笔触描述了厌食症的主观体验。对她来说,厌食症开始于14岁,几乎是一夜之间。她突然感到一种压倒性的需要,要控制自己吃进去的每一样东西,要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小、更轻、更”完美”。这种需要很快变成了强迫——她无法停止计算卡路里,无法停止称体重,无法停止锻炼。食物从生活的营养来源变成了敌人,每一口食物都伴随着巨大的焦虑和罪恶感。她的体重急剧下降,月经停止,头发开始脱落,手脚冰冷,全身覆盖着细小的绒毛(身体试图保暖的反应)。但即使她的身体明显在崩溃,她的大脑仍然告诉她,她还不够瘦,她需要继续减重。
弗里曼没有回避厌食症的恐怖。她描述了住院治疗的日常:强制进食,在护士监督下吃完每一口食物,饭后被禁止去厕所(防止催吐),每天称重,与同样患病的女孩们生活在一起,既互相支持又互相竞争谁更瘦。她描述了厌食症患者之间复杂的动态——她们理解彼此的痛苦,但同时也陷入比较和嫉妒,因为在厌食症的逻辑中,更瘦意味着”更成功”。她描述了医疗系统的局限:医生可以强迫她吃东西,可以监控她的体重,但他们无法改变她大脑中那个声音,那个不断告诉她”你不够好,你需要更瘦”的声音。治疗更像是一种遏制,而非治愈——目标是让她的体重恢复到不致命的水平,而不是真正理解和解决她为什么会生病。
在医院三年后,17岁的弗里曼”康复”出院了——她的体重回到了医学上可接受的范围,她学会了不在医护人员面前表现出厌食行为。但正如她在日记中写的,她感觉自己比以前更疯狂。因为她没有真正康复,她只是学会了隐藏。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她成为所谓的”功能性厌食症患者”——表面上她生活正常,有成功的职业生涯,有社交生活,但私下里她仍然被食物和体重的强迫性思维控制,仍然在与自我毁灭的冲动搏斗。厌食症像变色龙一样变异:有时表现为过度运动,有时表现为暴食后的极端补偿行为,有时表现为对身体的其他形式的控制和惩罚。
这种”康复但未痊愈”的状态是弗里曼书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医学通常将厌食症康复定义为体重恢复和月经恢复,但这忽视了心理层面的持续斗争。许多厌食症患者,即使体重正常,仍然被食物焦虑、身体厌恶和强迫思维折磨。他们学会了表演”正常”,在公共场合吃东西,避免引起怀疑,但内心的痛苦并未消失。弗里曼称这种状态为”用胶带粘起来的康复”——从外面看你是完整的,但里面仍然是破碎的。这种状态可以持续几年、几十年,甚至一生。它是一种疲惫的生活方式,需要持续的警惕来抵抗疾病的回归,同时假装一切都很好。
为了理解自己的经历并探索真正的康复是否可能,弗里曼在写作本书过程中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她采访了治疗厌食症的领先专家,了解自她住院以来医学对这一疾病的理解有了什么进展。她了解到一些令人震惊的新发现:厌食症与自闭症谱系障碍有显著的共病率,许多厌食症患者表现出自闭症特征,如刚性思维、对规则和秩序的需要、社交困难;厌食症与强迫症密切相关,许多患者同时患有强迫症或表现出强迫特征;厌食症可能与代谢率异常有关,某些人的身体对饥饿的反应不同,这可能部分解释为什么厌食症如此难以治疗。
弗里曼还探讨了厌食症的性别和年龄模式。虽然男性也会患厌食症,但90-95%的患者是女性。更重要的是,厌食症几乎总是在青春期开始——10到18岁之间。这不是巧合。青春期是女孩身体和社会身份发生剧变的时期:她们的身体开始性成熟,曲线出现,月经来临;社会对她们的期待也发生变化,从”孩子”转变为”女性”,这意味着要应对性化、物化、以及一整套关于女性应该如何外表和行为的规范。对许多女孩来说,这种转变是可怕的。厌食症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拒绝成长的方式——通过使身体保持青春期前的纤细和平坦,通过停止月经,来延缓或逆转成为女性的过程。
弗里曼敏锐地观察到,厌食症揭示了成为女性在父权社会中的固有困境。女孩被教导要”好”——顺从、安静、不占空间、不制造麻烦。她们被教导要关注外表,因为这是她们价值的主要来源。她们被教导要取悦他人,尤其是男性。但同时,她们也被告知要有抱负、要成功、要坚强。这些矛盾的期待创造了一种不可能的处境。厌食症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这些矛盾的一种扭曲的解决方案:通过控制食物和身体,女孩获得一种控制感和成就感;通过变瘦,她们既符合美丽标准又拒绝女性化;通过自我惩罚,她们既表达愤怒又将其内化,避免成为”坏女孩”。
书名”好女孩”正是对这一动态的讽刺性评论。厌食症患者往往是”好女孩”——成绩优异、遵守规则、完美主义、渴望讨人喜欢。她们的疾病在某种程度上是将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推向极致:要苗条,那就瘦到极致;要自律,那就控制到极致;要不麻烦别人,那就消失到极致。弗里曼指出,当我们称赞女孩”乖巧""懂事""不挑食”,当我们赞美女性的自制力和纤瘦身材时,我们实际上在强化那些可能导致厌食症的价值观。厌食症不是对正常价值观的偏离,而是将正常价值观推向病态极端的结果。
本书最动人的部分之一是弗里曼追踪当年与她一起住院的女性们的故事。二十多年后,她联系到其中几位,了解她们的人生轨迹。这些故事既令人心碎又鼓舞人心。有些女性真正康复了——她们建立了家庭、事业,学会了与食物和身体和平相处,虽然偶尔仍会听到厌食症的声音,但已经能够不被它控制。有些女性仍在挣扎——厌食症演变为其他形式的成瘾或心理健康问题,康复之路崎岖反复。还有一些女性没有幸存——厌食症夺走了她们的生命,通过心脏衰竭、器官损伤或自杀。
这些不同的结果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厌食症康复没有保证。即使是最好的治疗、最支持的家庭、最坚强的意志,也不能确保康复。某些患者康复,某些不能,我们仍然不完全明白为什么。这种不确定性是疾病最可怕的方面之一——既对患者,也对他们的亲人。它也暴露了我们的医疗系统和社会对精神疾病理解的局限。我们习惯于认为疾病有明确的原因和治愈方法,但对于厌食症这样的复杂精神障碍,现实远没有那么简单。
然而,弗里曼的书最终是一个希望的故事。在写作过程中,在与幸存者交谈、与专家讨论、重新审视自己经历的过程中,弗里曼自己经历了一次更深层的康复。她学会了区分自己的声音和厌食症的声音。她学会了自我同情——理解她的疾病不是她的错,不是她软弱或虚荣的证据,而是她试图应对无法承受的痛苦的方式。她学会了在不完美中接受自己——她可能永远不会完全”治愈”,可能总会有某种脆弱性,但这不意味着她不能拥有充实、有意义、快乐的生活。
弗里曼向读者传达的核心信息是:生活可以被享受,而不仅仅是被忍受。对于长期与厌食症或其他饮食障碍斗争的人来说,这可能听起来不可思议。当你每一餐都充满焦虑,当你每次照镜子都感到厌恶,当你的大脑被食物和体重的强迫性思维占据时,“享受生活”似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概念。但弗里曼坚持认为,康复是可能的——不是完美的、没有挣扎的康复,而是一种生活变得可以忍受,然后变得可以享受的康复。这需要时间、支持、治疗,有时需要药物,总是需要巨大的勇气和耐心。但它是可能的。
这本书也是对美国近3000万饮食障碍患者(全球数字更高)的一种见证和声援。饮食障碍包括厌食症、暴食症、暴食障碍等,影响着各个年龄、性别、种族和社会阶层的人,虽然年轻女性仍然是最高风险群体。这些疾病往往在沉默中发生——患者因羞耻而隐藏,家人因不理解而忽视,社会因污名化而回避。弗里曼的公开讲述打破了这种沉默。她展示了一个公众人物、成功记者、有天赋的作家也可以是,也曾经是,精神疾病的患者和幸存者。她的故事让其他患者感到被看见、被理解,不那么孤独。
从女性主义视角来看,《好女孩》是对身体政治的深刻批判。弗里曼虽然没有将自己的作品明确标记为女性主义,但她的分析本质上是女性主义的。她揭示了厌食症如何与父权社会对女性身体的控制和物化密不可分。女性的身体从来不属于她们自己——它被时尚产业、医学机构、男性凝视、家长式的保护、国家的生育政策所规训和控制。厌食症是这种外部控制内化的极端形式——女性成为了自己的监管者,执行着比任何外部力量更严厉的规训。
弗里曼也探讨了医疗父权制在厌食症治疗中的体现。她回忆起治疗中的屈辱:被迫脱衣称重,被护士监视如厕,失去隐私和自主权,被当作需要被控制的不服从的身体而非有思想和感受的人。虽然医护人员的意图是挽救生命,但方法往往是家长式和剥夺尊严的。更糟的是,传统治疗主要关注体重恢复,将女性身体简化为需要达到的数字,却很少关注导致疾病的心理、社会和结构性因素。这种治疗范式本身反映了社会对女性的简化——将她们视为需要被塑造成适当形状的身体,而非需要被理解和支持的完整的人。
书中还触及了阶级和特权的问题。弗里曼来自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能够承受私人精神病院的费用(虽然非常昂贵),能够获得专业治疗。她承认这是一种特权——许多患有饮食障碍的人没有机会获得这样的治疗,要么因为经济原因,要么因为她们的疾病没有被识别(饮食障碍在有色人种社区中经常被忽视,部分因为刻板印象认为这是”白人女孩的疾病”)。治疗的可及性和质量与经济状况密切相关,这意味着康复机会也是不平等分配的。
弗里曼的写作风格使这本可能非常沉重的书变得可读甚至有时有趣。她用”敏锐的叙事、扎实的研究和温和的幽默”(《华尔街日报》语)讲述她的故事。她不回避痛苦和黑暗,但也不沉溺于其中。她以记者的清晰和精确描述事实,以幸存者的洞察力分析意义,以作家的技巧创造引人入胜的叙事。她的幽默不是轻率的,而是一种应对机制,一种在绝望中保持人性和尊严的方式。这种语调上的平衡使得书籍既诚实又有希望,既严肃又可接近。
《纽约时报》称这本书”引人入胜”,这个评价恰如其分。这是一本很难放下的书——部分因为故事本身的戏剧性和情感强度,部分因为弗里曼作为叙述者的诚实和洞察力,部分因为主题的普遍共鸣。即使读者没有亲身经历过饮食障碍,也很可能认识经历过的人,或至少熟悉与身体形象、食物焦虑、完美主义和控制的斗争。弗里曼的故事是个人的,但它触及的主题是集体的,尤其是对女性而言。
这本书对中国读者也有特殊的相关性。虽然饮食障碍在中国的统计数据相对较少(部分因为诊断和报告不足),但有证据表明这些疾病在中国年轻女性中正在上升,尤其是在城市化、西化的环境中。中国女性面临着与西方相似的矛盾期待:要成功但要谦逊,要美丽但要端庄,要现代但要传统。社交媒体上充斥着”A4腰""锁骨放硬币""反手摸肚脐”等病态的身体标准。同时,对心理健康问题的污名化使得许多患者不敢寻求帮助。弗里曼的书提供了一个理解这些问题的框架,以及一个希望的信息:康复是可能的,谈论它不是羞耻而是勇气。
最终,《好女孩》是一本关于韧性和自我接纳的书。弗里曼经历了可怕的痛苦——疾病本身的痛苦,治疗的痛苦,与康复斗争的痛苦。但她幸存下来,不仅幸存,还创造了一个有意义的生活和职业,还能够讲述她的故事,帮助他人。这不意味着她的生活是完美的或她已经”战胜”了厌食症——她诚实地承认,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她仍然有艰难的日子。但她找到了一种与疾病共存的方式,不让它定义或控制她的生活。她学会了倾听自己真实的声音,而不是疾病的声音。她学会了善待自己的身体,而不是把它当作敌人。
对于正在与饮食障碍斗争的人来说,这本书是一个强大的提醒:你不孤单,你的痛苦是真实的,你值得帮助和康复,你的生活可以变得更好。对于照顾患者的亲人来说,这本书提供了深入了解患者内心世界的窗口,帮助理解这种疾病不是关于虚荣或寻求关注,而是关于深刻的痛苦和恐惧。对于所有读者来说,这本书是对我们社会如何对待女性身体、如何定义美丽、如何理解精神疾病的批判性思考的邀请。
哈德利·弗里曼以巨大的勇气和技巧写下了她最私人的经历,创造出一部既是回忆录又是调查研究、既是个人见证又是社会批判的作品。《好女孩》是任何关心心理健康、女性权利、身体政治或只是人类痛苦和韧性的人的必读之作。它提醒我们,最大的勇气不是从不跌倒,而是一次又一次地爬起来;最深刻的自由不是完美,而是接受不完美;最真实的康复不是消除所有痛苦,而是学会与它共存,并找到快乐和意义。对于那些仍在黑暗中挣扎的人,弗里曼的书是一盏灯,照亮了通往希望的道路。
书籍信息
相关主题
相关推荐
读书讨论
分享您对这本书的感想和看法,与其他读者交流见解
加入讨论
分享您对这本书的感想和看法,与其他读者交流见解
评论加载中...
 在亚马逊购买
在亚马逊购买